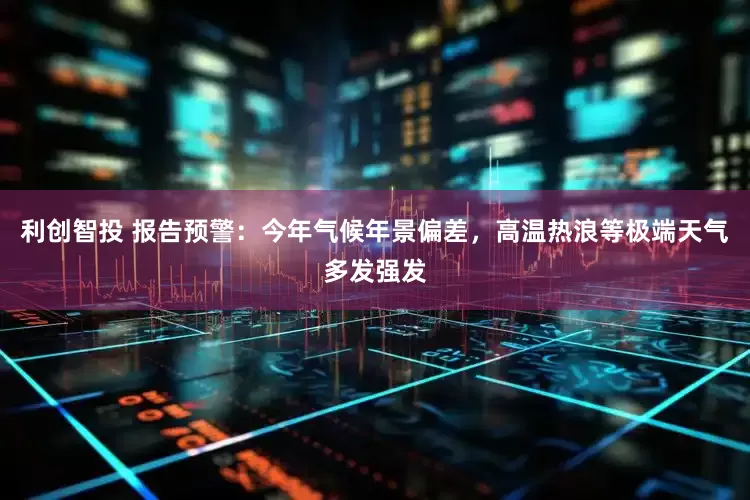蒋艳萍
文 | 蒋艳萍
●岭南名山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其书写不仅是对岭南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文人通过想象和文字构建的审美共同体。名山之所谓“名”,必须是可被反复观看、书写、题咏的“文本化风景”
●通过对岭南名山的书写,文人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情感的审美世界,汇聚远山、边地、家园等多重浪漫想象,成为构筑“诗性岭南”精神传统的重要元素
岭南名山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其书写不仅是对岭南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文人通过想象和文字构建的审美共同体。名山之所谓“名”,必须是可被反复观看、书写、题咏的“文本化风景”。它们被自然造化所生发、被历史文化所浸染、被诗文图绘所反复书写,从而成为某一地域人们共享的精神坐标与审美象征。
 日斗优配
日斗优配
山川形胜、造化钟灵:
岭南名山的地理基因
岭南地处炎方,五岭横亘、南海环抱,在漫长的地壳运动中,逐渐形成山川纵横、陆海相荡、地理构成交错复杂的地貌景观。被誉为“广东四大名山”之罗浮山、丹霞山、西樵山和鼎湖山,或洞天幽深,或丹霞赤壁,或翠岫流泉,或山湖掩映,天然具备“可游可观可诗可画”的审美可感性。
屈大均言丹霞山锦石岩:“岩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黄白红绿不一,倒生石腹,朵朵可以攀摘……其下临大江,明砂绣发,清岚镜莹,外则远近峰峦,争奇竞峭,多上丰而下削,状若倒生苞笋,盖山水之绝怪处也。”“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特殊地貌,吸引了明朝遗民李永茂、李充茂兄弟选择到仁化避世隐居,认为:“是山(长老峰)也,有险足固,有岩足屋,有樵可采,有泉可汲,其亦避世之奥区乎?”
罗浮山全境拥有众多大小山峰、洞天美景、石室幽岩,山中景色如画。主峰飞云顶山势陡峭,宛若倚天长剑,峰顶却盘圆平坦、花草并茂、云雾缭绕。南宋名臣李昴英曾登飞云顶,感受着云生足下、雾霭天低、飘飘然如入仙境之快乐:“俄身在山巅,飘飘然坐鹏背,御长风,宇宙茫茫,八极一视,某州某山,仿佛可指点。云气猝起衣袖,莫认对面。”夜半观日更是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倾力而为,先有刘禹锡夜宿飞云顶,以雄浑磅礴之势刻录下这一波澜壮阔之景:“咿喔天鸡鸣,扶桑色昕昕。赤波千万里,涌出黄金轮。”复有苏轼、陈恭尹登临罗浮绝顶观日,与之展开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江潮应瀑声千里,海气成霞色万重。一线日轮天已晓,远鸡才报下方钟。”
无论是丹霞山的特殊地貌,还是罗浮山的特有天象,均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植入文人书写中,形成“未见其山,先闻其色”的鲜明记忆,以其独有的标识性吸引后来登览者一睹为快。
历史演绎、人文浸染:日斗优配
岭南名山的文化累积
“名山”作为附着于自然地理之上的文化符号,其生成与书写始终被政治、经济、地理与文化合力塑造。南方的名山书写与话语建构由边缘渐入中心,恰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同频共振。岭南地处“南方之南”,其名山书写的历史伴随岭南文化一路生长,在中国整体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岭南地区山川秀美,文化底蕴深厚。如罗浮山被誉为“五岭众山皆拱附”的“百粤群山之祖”,自古以来便是道佛儒三家共存之地,文化包容并蓄,其中仙道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魏晋以后更被纳入道教名山系统。清代王朝恩指出:“天下四大名山曰普陀、峨眉、五台、九华,皆菩萨道场,而罗浮则神仙之洞府。”自古以来,留下了浮山泛海、安期天饮、稚川炼丹、师雄梦梅、东坡啖荔、洞天药市等无数美好的传说和典故。
西樵山有“珠江文明灯塔”之称,为岭南著名古火山,早在四万年前已有先民活动。明正德年间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儒学大师相继入山兴修了四大书院,收徒设教,传播学问,使西樵山一跃成为明代理学重镇,更被盛赞:“西樵者,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青年康有为于白云洞三湖书院读书二载,终日在石窟瀑布、甘泉密林中潜心修学,新学旧知尽相收纳,萌发出“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的维新思想。白云洞留下了这位年轻人在激烈的思想启蒙中徘徊的步伐,西樵山被后人誉为“戊戌变法的摇篮”。
偏安一隅,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亦孕育了岭南山水特殊的使命,使其成为南来北往文人迁客怀古叹今、寄托身世、抚慰心灵之地,亦成为历次王朝更迭之际汉文化退守与存续的重要根据地。“庾岭南北通道”“峡山诗路走廊”“丹霞禅宗祖庭”“崖山吊古之地”“鼎湖禅林圣地”……一张张文化名片,为岭南名山加持,赋予其厚重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文学形塑、精神浇筑:
岭南名山的美学情怀
古往今来,岭南名山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反复书写,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地理意象。
不同时期的岭南名山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风味。魏晋时期,处于文化中心的中原人书写岭南,充满了远山想象,呈现出或莽荒化或神圣化的倾向。一方面,中原儒生对处于华夏边缘的岭南形成固有印象:山川多毒虫、溪谷多瘴疠、南越多物怪。另一方面,随着神仙道教创始人葛洪入粤和道教洞天福地体系的形成,南粤山川被描述为多洞窟奇峰、多仙芝灵草、仙人出没之地。岭南名山亦向久远的时代攀援着亲缘,如鼎湖山黄帝铸鼎、韶石山虞舜奏韶乐、白云山郑安期驾鹤飞升,等等。
唐宋时期,随着贬谪文人和名道名僧的增多,特别是张九龄、刘禹锡、韩愈、苏轼、杨万里等文学大家对岭南名山的居留驻足、深入接触,岭南名山书写一改以往的高冷寥远荒野风格,由仙境书写慢慢转向幽境书写。仙境描写强调其神秘与超凡,往往以夸张、奇幻的笔触描绘超脱尘世的意象,引发人们对仙境的向往。幽境描写则多聚焦于山中自然景物的细腻刻画,展现山林的宁静清幽之美,引发人们的隐逸情怀。
元明清时期,岭南理学大昌,书院文化兴盛。近古以来,大量岭南士子崛起,在清初诗坛更是形成与中原、江南三足鼎立之势。少时筑室山间读书,致仕退隐山间传道,他们笔下的岭南名山是自证身份的名片,是温暖可人的家园,也是很多人回不去的乡愁。
当一个人身处异乡时,身份的归属变得尤为重要。身处异乡或宦居在外的游子更容易通过对家园的回望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表达对家乡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以名山为字号成为他们惯常的做法,如屈大均号“罗浮道人”、郑观应号“罗浮待鹤山人”、康有为号“西樵山人”等,这种以家乡之山标榜自己身份的做法无疑彰显了岭南士子对家乡文化的自豪和自信。他们对家乡山水的反复书写使岭南名山成为岭南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了岭南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对外传播。
当家园变得可亲可爱,无需向外攀爬,亦可吸引外客栖居游观,岭南名山更是成为岭南文人邀请中原士子交游的最好去处。他们以经典景观的寻绎命名、诗画雅集和社交活动,助力岭南之地声名的远播。他们跳出游仙玄想,以纪实的手法记录游山体验,从而催生明清时期岭南山水纪游诗与实景图的创作热潮。于是乎,罗浮酥醪十景、艮泉十二境、西樵白云洞二十四景、羊城浮丘八景等景观之生成与再造,成为诗画交游的重心,亦成为岭南诗派、画派成长的温床。
总而言之,岭南名山书写作为一种审美想象共同体,不仅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还促进了岭南文化的传播,增强了岭南人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对岭南名山的书写,文人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情感的审美世界。这个审美世界不仅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还连接了岭南与外界,凝结了岭南人自我书写、文化自证的记忆,同时包含中原人由远观、走近到接纳岭南的心理历程,汇聚远山、边地、家园等多重浪漫想象,成为构筑“诗性岭南”精神传统的重要元素。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项目(GD25LN33)研究成果日斗优配
新宝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